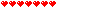那是在90年代,当时还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但性革命已经席卷了全国。我们是通过报纸《Hand to Hand》的约会栏目认识的,互相写信,然后去Poste Restante邮局领取。他自己也不再是单身,认识了一个已婚女子,他们互相打电话,约定在某某日期见面。那时,餐馆和咖啡馆的数量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我们下午在Pelmennaya咖啡馆见面,每个人都很穷,没有车,没有钱,但性召唤并吸引着每个人。我们喝着酒,聊着天,聊着坦诚的话题,我看到她脖子上的静脉已经在跳动。这样的谈话让我们非常兴奋。那时候,只要拿着护照去酒店,作为夫妻,几乎没有桑拿,我们走到街上,旁边是一栋新的高层建筑,楼梯平台和公寓是分开的着陆。我们去了那里,那里有一个对讲机,我们刚出现,突然一个人走了出来,我们就潜入了那里。 我们跑进电梯,在某个顶楼紧紧地贴在一起,到处抚摸、抚摸。电梯停下来,门打开,我们纠缠在一起亲吻,一个年轻人站在我们面前微笑。我们跑到楼梯平台,再次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人都激动得浑身发抖。现在是夏天,她穿着喇叭裙和衬衫很温暖,我把她转向窗户,取出她的乳房,掀起她的裙子,进入她滴水的阴户。她靠在窗台上,我用力操她,我们同时高潮,我们站在那里,气喘吁吁,腿发抖,我说我快要幸福死了,她回应说对面的男人肯定死了。我向窗外望去,房子就在拐角处,十米外的阳台上有一个男人站着,紧张地抽烟,我从窗户跳开,我们笑得像个白痴。显然,当她在男人面前摇晃奶头、被后入式操时,她很兴奋,因为她没有立即说什么。
2 小时 9 分 47 秒后发送:
这些熟人中的一个让我和一个在我的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孩在一起,但稍后会详细介绍。坐在咖啡馆里喝酒并谈论各种话题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在性话题上。但到了秋天,天黑得很快,交通也越来越少,我们决定回家,像一位英勇的绅士一样,决定陪我们回家。 而我们在电车上,在第二节车厢,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谈论性幻想,接吻,在酒精和兴奋的作用下,到处互相触摸。她在我耳边低语: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口交!?是的,但是你是怎么猜到的?她轻轻地将我坚硬的阴茎从苍蝇中取出,开始贪婪地吸吮。不幸的是,两站后我们就得下车了,我没有时间走完。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出了真相,这句话简直要了我的命:她并不羞于用舌头操一个男人的屁股。 当我们进入入口时,我们都非常兴奋,准备好迎接任何事情,在温暖的散热器旁,我脱下她的裤子,开始用狗式操她,她已经全身都漏了。由于路过的居民干扰,我们无法完成,我们决定推迟到晚些时候。其中有不少。
- Quick links
- Light mode
- Dark mode
- ⛳ Active Topics ⤇
-
- by Guest_117 20 Mar 2025, 02:16 是谁打破了自己的童贞?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Guest_429 25 Aug 2024, 16:18 谁自慰做什么?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圣诞节_圣诞节 13 Aug 2024, 18:32 4ALL 论坛的人都来这里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安卓20081 13 Aug 2024, 18:26 老婆的屁股。照片。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亚历克斯会 13 Aug 2024, 18:26 自慰时谁将精子倾倒在哪里?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拉吉 13 Aug 2024, 18:26 照片 - 无耻妈妈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刷子 13 Aug 2024, 18:25 给女人看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色诺芬 13 Aug 2024, 18:25 激发想象力的图片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我们发生性关系 13 Aug 2024, 18:23 同性恋第一次故事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圣诞节_圣诞节 13 Aug 2024, 18:22 History_25_我变得可用并且我喜欢它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邮政 13 Aug 2024, 18:22 女儿和父亲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亚历克斯会 13 Aug 2024, 18:14 自慰时爱抚乳头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亚历克斯会 13 Aug 2024, 18:11 如果你的女士喝醉了,你喜欢舔阴吗?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卡洛斯 13 Aug 2024, 17:35 你的女士们的照片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发生的事 13 Aug 2024, 17:32 小乳房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安卓20081 13 Aug 2024, 17:27 你给你妹妹打几分???并送你的姐妹或母亲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拉萨罗姆 13 Aug 2024, 17:12 我现在在听什么?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色诺芬 13 Aug 2024, 17:05 一张无害的照片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令人兴奋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阿列克谢·奥梅尔琴科1957 13 Aug 2024, 17:04 女生评价男人的鸡鸡 View the latest post
- by 谢尔盖12345 13 Aug 2024, 15:57 人妖 View the latest post
- Login
- Register
- 爱情艺术论坛
-

- All times are UTC+08:00
- Delete cookies
Powered by phpBB® Forum Software © phpBB Limited
Time: 1.531s | Peak Memory Usage: 14.15 MiB | GZIP: On